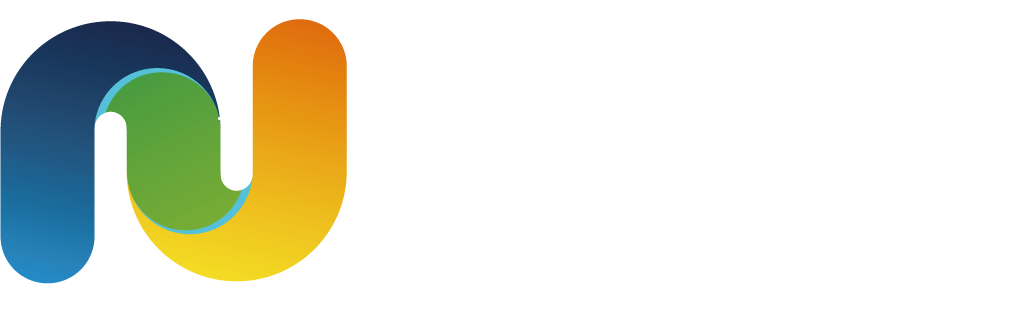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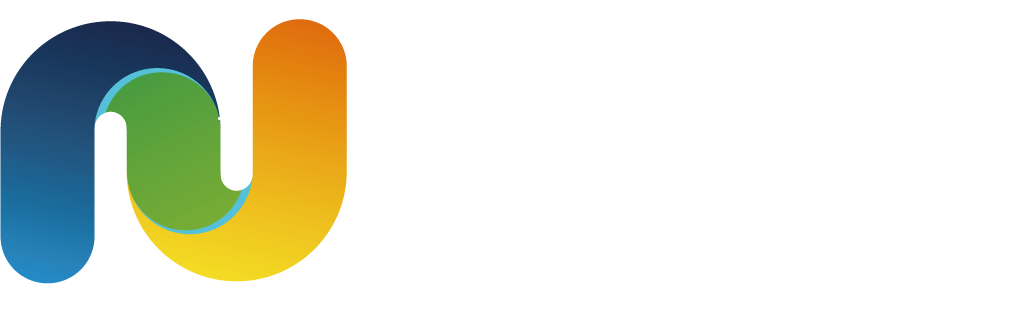
编者的话
匠心守拙 上下求索
“工匠精神”在大众语境之下,形容的是工匠对产品精雕细琢,孜孜不倦的精神理念,是匠人们用岁月和情感酿造出的最显著、最可贵的行为特质。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也不乏这般纯粹的“匠人”。他们敢于用时间来验证,就像锲而不舍的“乡土实验家”,以缓慢、精益求精的方式打磨自己的事业和人生,力求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
当一种形同天书且不被现代社会广为使用的文字语言濒临消失,是选择放弃还是重新拾起?水书先生杨胜昭选择了后者,他的理由也很简单:水书是“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一份子,也是水族人民的文化基因。在《三都自治县羊瓮村:将古老水书带入当代》一文里,杨胜昭选择用漫长岁月书写自己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致力于将祖先的智慧融入现代化社会中。
高级农艺师朱子丹也是一个执着的人,如何种好蔬菜是她29年来的不懈追求。在《都匀市良亩村:给农业种上科技“芯”》一文里,为了解决基地问题,找到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她把家安在乡下,倾注所有时间心血做调查研究,直至抵达目标终点。她的身上有着一种质朴的“守拙”气质,纯粹且坚韧,是她对“工匠精神”的诠释。
在快速发展时代,如何不疾不徐,做一件长久的事?姚其学和李福泉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他们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因循守旧,在辛勤耕耘的过程中扩大发展的截面。如果没有“铁打”的身板和毅力,很难坚持这么多年。这种“匠人”的姿态,让他们在眼底的方寸空间里自由驰骋,通往更广阔的道路。正如作者在《福泉市双谷村:梨花再开放》一文中写的那样:他自认自己就是那头牛,埋头耕耘,最期待的就是见到来年满山梨花再开放。
当代知名社会学家和思想家理查德·桑内特在他的《匠人》一书中说,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匠人,因为匠心——把事情做好的欲望是植根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人性冲动。成为一个匠人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如何保持匠心才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杨胜昭、朱子丹、姚其学、李福泉等乡村建设者,尽管一路走去困难重重,但他们乐于在守拙之中寻找变体、不断探索,走在时代浪潮之中。他们的“匠心”在时间的淬炼下坚定,“匠魂”在不懈的攀爬中沉淀。这让我想起《离骚》里,那坚定又执着的人生之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向秋樾
(图片均由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彭芳蓉 摄)
三都自治县羊瓮村:将古老水书带入当代

水书传承人杨胜昭。
与杨胜昭见面有些匆忙,我来不及提前了解他的故事,以至于当他说“其实我也不懂水书”时,我竟差点把这谦虚当真了。直到结束了那场漫长的交谈后,我才回味过来,杨胜昭所说的“懂”和我理解的“懂”或许不是一个意思。
我们见面的地点是在县城里的非遗体验中心。这是一个近几年新建的体验中心,马尾绣、水书等水族的非遗项目在馆内各占一处空间。不过,在这个汇集了水书文化的空间中,被返聘到黔南州水书文化研究院从事水书译注和水书抢救及申遗工作的杨胜昭,频繁提起的却是另一个空间——羊瓮村。
那里是杨胜昭成为水书先生的起点,也是他付诸了大半辈子心血的地方。
杨胜昭的父亲是水书师,而杨胜昭也在13岁时就被伯父杨锦村收为徒弟。在过去,水书师在水族农村是一项神秘且令人敬畏的职业,水书像甲骨文又像金文,而婚丧嫁娶、立屋建房,甚至春耕开种的时辰都要根据水书中的提示来决定。
正因蒙上了这层神秘面纱,“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也成了水书师迭代传承的首要原则,水书师需在家族内亲自挑选一名德才兼备且秉性善良的人,才能将这来自远古的“密码”传授下去。显然,杨胜昭就是伯父眼中符合条件的人。杨胜昭虽然年轻,却清晰地感受到一种不可违抗的仪式感。几乎每个农闲的夜晚,晚饭过后,伯父便来到家里,掏出纸张泛黄、写满神秘文字的书卷,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他认读。
水族文字虽然只有几百个字,但一字多音、一字多义,且在不同的组合和语境中会产生不同的含义,但就算认全了那些水族文字,人们也不一定能破解水书卷本中所记载的秘密。水书最大的难点在于,卷本中所记载的内容往往是记一半、藏一半,文字所记录下的都是高度凝练的内容,真正要读懂背后的文章,需要水书师来唱诵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的部分,这个部分全靠一代代水书师口传心授。
此后的10年里,那些与水族生息繁衍息息相关的秘密,跨越不知多少个世纪进入到杨胜昭的脑海中。到了第一次被允许运用水书时,杨胜昭已30岁,在羊瓮小学当了许多年的乡村教师。“打工潮”将青年人带出村庄,曾经神圣且神秘的水书师成了人们敬畏但不再向往的职业,身为教师的杨胜昭成了羊瓮村唯一的一个水书师,他不希望自己是最后一个,他想做点什么。
后来,在羊瓮小学的课堂里,这种来自远古的神秘文字出现在黑板上,那低沉而优美的吟诵,也加入了稚嫩的声音。精通水族习俗,又掌握了大量水书文字的杨胜昭,知道水书并不仅是用来占卜良辰吉日的工具,那些文字背后蕴藏的内容,囊括了水族的起源、迁徙等历史,甚至囊括了水族人对宇宙万物的理解和智慧。既然家族中无人传承,那他就只能打破千百年来“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不成文规定,先让水书活下来,再来谈规矩的事。
羊瓮小学的不少学生多少认识了一些水书文字,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懂得这文字背后的价值和意义。直到杨胜昭从羊瓮小学校长的职务上退休之前,这里的水书传习课几乎没有间断过。
早在2002年,水书就已纳入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06年,水书又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那之后的10余年里,杨胜昭常常陷入一种复杂的心绪中,他时常听闻年长的水书师相继离世,全县的水书师人数从300多人减少至200多人,但他也常常听到一个新词:“抢救性保护”,这是三都自治县乃至整个贵州民族文化学界正在做的事。2015年,黔南州水书文化研究院向他发来邀请,贵州民族大学也向他抛来橄榄枝,请他正式参与到水书的抢救保护中。杨胜昭的退休生活就是这样忙碌起来的。
2016年,杨胜昭在一次县里有关水书保护的会议上情绪激动、言辞激烈。他主张,像自己在羊瓮小学时那样开办传习班传承水书。然而,这一主张遭到不少年迈的水书师反对,他们始终认为“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规矩不可破。
“中国56个民族,拥有自己的文字的少数民族有多少个?水书作为我们水族人自古传下来的文字,记录了我们的民族历史和祖先古老的智慧。现在,各位的家族中还有几个年轻人愿意主动学习水书?如果再不打破陈规,水书的传承还有什么希望?”杨胜昭慷慨激昂的讲演,压下了那些反对的声音。很快,“水书习俗少儿弟子班”正式开班,8名水族少年拜在杨胜昭门下,其中有4名是女弟子。实际上,在开这个传习班之前,他早已于2015年破例招收了三都自治县档案史志局的女局长潘中西为弟子,潘中西也因此成为三都首个水书女弟子。
在我见到杨胜昭时,他已经66岁,唇上的胡须开始发白。谈到县里的水书师时,他有些忧伤:“去年,中和镇的水书师杨胜凡也走了。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懂的比我多多了。他活了整整100岁……”杨胜昭眼神暗淡,100岁的高寿对于一个精通水书文化的老人而言依旧太短。
很快,杨胜昭的情绪又提了起来,“这里(县非遗中心)也经常搞水书文化的研学活动,我也来讲过。”他又提起在贵州民族大学担任的工作:“我在民大(贵州民族大学)还担任着特聘讲师的工作,现在有不少博士生也学会了水书文字。要翻译和整理的内容太多了,我尽量做,做不完的还有后面的人接着做。”
在见到杨胜昭的一个多月之后,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他在三都民族中学开展“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的消息。照片里,他刮掉了发白的胡须,穿着黑色的水族服装,神采飞扬。不知在吟诵出那些伯父口传的古老文字时,杨胜昭是否有某个瞬间感觉自己回到了羊瓮小学的课堂,与那稚嫩的童声一起,将祖先的智慧带到这个现代化的世界中。
都匀市良亩村:给农业种上科技“芯”

朱子丹与她指导种植的冬瓜。
时隔近半年,我终于见到了朱子丹。
“一年365天,我可能有300多天都在村里,办公室不常来。”在都匀市区内的老式办公楼里,朱子丹抱歉地说。朱子丹确实太忙了,我们这次见面定在周日,她前一天晚上才刚从距离都匀市最远的一个村寨回来。
“算起来,我工作也有29年了。”回想自己的从业生涯,这个数字似乎让她有些感慨,“10多年前还没这么忙,后来产业结构调整、脱贫攻坚开展,要负责的工作就多了起来。”朱子丹是长期从事蔬菜技术推广的高级农艺师,现在在都匀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发展中心任副主任,在贵州省产业革命专家团队建立以后,她也成了茄子、菜豆小分队的一员。
她所说的“10多年前”大概是指1992年至2012年期间。1970年在都匀出生的朱子丹,从小在城市长大,1992年从原贵州农科院园林专业毕业后,便一脚踏进泥土里,开启与土地和种子打交道的生活,一直把心思都放在技术攻关、技术指导和基础设施的管理上。直到2012年,朱子丹来到墨冲镇良亩村。未曾想到,她在此扎根后所做的工作成为推动黔南州成为大湾区“菜篮子”的重要一环。
这一年,产业结构调整的浪潮在都匀刚刚掀起,当地要求先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做蔬菜基地试点。良亩村是都匀的粮区,历来以种植水稻为主,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资源优势让良亩人引以为傲。人们习惯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朱子丹及其团队的到来令人无法理解。
朱子丹和乡镇干部、村干部一起挨家挨户动员村民流转土地,目标是1000亩。而听说要在土地上改种蔬菜时,部分村民头摇得像拨浪鼓,一口回绝了这一请求。在以水稻为生的农户看来,不种水稻改种蔬菜,简直就像在砸人饭碗。一番辛苦下来,目标只完成了不到2/3,朱子丹等别无他法,只能先用眼下这六七百亩土地开启试验。
茄子、玉米,这些市场需求较大的蔬菜在良亩的土地里安了家,朱子丹又马不停蹄地考虑销路问题。拉着蔬菜去批发市场碰运气的传统方式肯定行不通,那对农户来说不够有保障,对口的销路才是解决办法之道。
那时,广东省是黔南州的对口帮扶省份,广州这个对蔬菜需求量极大的一线沿海城市自然成了朱子丹的目标。她与团队前往广州最大的江南果菜批发市场,打算在那里找一个与良亩有缘分的人。在这里,朱子丹与林炳锡结识,对方来到良亩,愉快地与当地合作社达成合作协议,将那600多亩土地打造成为茄子基地,由朱子丹团队全力提供技术支撑。
此后的几年中,朱子丹的工作就像在滚雪球。涉足招商引资引进了外地企业,便要配合企业需求筛选蔬菜品种、提升合作社规模、提升农民种植技术;规模扩大,就要继续拓展市场,所以要继续外出对市场进行考察;蔬菜业务范围拓宽,引进的企业也要得到提升,所以必须带着企业参加各类展会,必要时还要参与销售……同时,为了提升基地品质,良亩村的基础设施也在一点点改变,产业道、机耕道一条接着一条铺进村里,乘着新农村建设的东风,村里的房屋也与这现代化农业示范地的气质匹配起来,村寨面貌焕然一新。
2014年后,脱贫攻坚全面展开,产业结构调整的节奏更快。朱子丹几乎天天都要往农村跑,但仍觉时间不够用,她和团队索性做了一个决定:收拾行囊,住到乡下去。
几年过去,朱子丹总算啃下了墨冲良亩1000余亩蔬菜试验地这块“硬骨头”,同时也将过往经验传递到都匀其他乡镇,推动了多个蔬菜责任田的发展。到2018年,蔬菜专家李桂莲、孟平红及其科研团队专家们来到都匀与朱子丹见面,提出由朱子丹领衔组建科研团队,承担贵州省蔬菜产业科技扶贫“321”项目(2018-2020年)的想法。
“321”项目是贵州省委、省政府制订的《贵州省发展蔬菜产业助推脱贫攻坚三年行动方案》中提出的作为蔬菜产业扶贫的科技支撑。简单来说,该项目是省农科院在全省高、中、低海拔进行多年试验示范的一项科研成果,采用间作、套作、复种等多种模式,配套高产栽培技术,以达到亩产3万、2万、1万的产值。而都匀良亩则作为中海拔地区的代表,要打造出一个项目示范地。
生活更加马不停蹄。朱子丹一边在良亩基地不停做品种试验,筛选优良蔬菜品种,一边撰写各种项目方案、规划、调研报告。用了2年多时间,她在这里筛选出50多个优良蔬菜品种和适应都匀市种植“321”高效栽培模式11套。
扎根在良亩村的几年里,朱子丹还有另一个令她欣慰的收获。
李国香,一位与朱子丹年龄相仿的良亩村农妇。她很早就开始在良亩蔬菜基地打工,几年过去,已经成为一位“职业农民”。因为“321”项目的推广,基地几乎没有农闲的时候,李国香一年四季几乎都有工作干。而长期跟在朱子丹身边,李国香不仅学到了不少种植技术,也学会了如何管理基地、管理农民团队。
像李国香这样的“职业农民”在良亩这个现代化的农业基地里还有20多位。“做科技推广的目的就是为了农民掌握更好的技术,李国香他们就是最好的代表。不是吗?”朱子丹满脸笑意地说。
2019年,贵州省蔬菜产业科技扶贫“321”项目在都匀的试验区取得不少突破性成果,朱子丹和她所在单位也因此同时获得贵州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当然,这并不是她从业生涯中获得的唯一奖项,早在2016年,她就因那几年的工作成效获得过农业部授予的全国农业先进个人,除此之外,从黔南州到贵州省的各级奖项她也有不少。
“你看现在的良亩村,真的很漂亮。”朱子丹打开手机,很快翻找出在良亩工作时拍摄大量图片,广袤的蔬菜基地,一片郁郁葱葱的景象确实十分喜人。“现在良亩的环境变好了,接下来我们还计划在那里打造观光步道,向农旅融合的方向来推动。”朱子丹像是又回到良亩的基地中一样,脸上写满了憧憬。
福泉市双谷村:梨花再开放

姚其学(右)和李福泉查看果林。
姚其学和李福泉坐在圆桌旁,身后是一片修剪整齐的梨树林。李福泉把手搭在桌子上,手掌宽大,骨节突出,手背上布满青筋,指甲缝里还有长久难以洗去的泥土。两人脸上刻满了深深浅浅的皱纹,不过,姚其学显然更年长一些。
他们聊天的时候不时回过头去望向那片梨树林,那是他们梦开始的地方。姚其学呵呵笑着,指着身后,道:“当年最早开垦的就是这一片,186亩,那时候我才30来岁。”李福泉笑眯了眼,搭话道:“我更年轻,才22岁,还什么都不懂哩。”
双谷村美如画卷,偶尔会让姚其学和李福泉感到有些梦幻。在回忆往昔时,他们不时停下来感叹:“当初谁能想象双谷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人在陷入温饱的挣扎时,确实不敢产生这样越级的“妄想”,所以,当初姚其学决意要加入生产队成立的果林场时,家人的极力反对便显得合情合理。
“你怕不是疯了?饭都吃不饱你要去种果树?管好家里的土地吧!”30多年前,无论是父母还是妻子,“战线”都非常统一,认为姚其学这30多年算是白活了,竟然作出这种异想天开的决定。姚其学却不这么认为,他并不是在孤军奋战。
1985年,乡政府安排成立果林场,派技术人员试种果树。尝遍了世间酸甜苦辣的姚其学,虽不知道种下的东西能否带来收益,不过,他依旧乐观,心想:“社会总是在发展,无论好与坏,总归会有一个结果。”而此时,20出头的李福泉还是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他每天只顾得上眼前的温饱。“再苦也不会比现在更苦。”李福泉加入到姚其学的队伍中。两人带着护林员们一番折腾,这片山坡换上了新衣。
刚种下梨树后的那几年,姚其学和李福泉一直在苦熬。梨树最快3年挂果,但人每天都要吃饭,他们便在果林间种下西瓜、玉米等短期收益的蔬果,勉强维持着生活。为了便于看护树林,姚其学和李福泉等人在果园旁边用空心砖搭起简易棚屋,4个人轮守在那里。入夜,山坡上唯一的亮光便只有天上的月亮和点点繁星,年轻力壮的青年只能借着工棚里昏暗的灯光陷入无尽遐想。白天的日子也不好过,渴了便到田里舀水,一边喝一边数着面前的蝌蚪,累了便在林子里找一个大南瓜当凳子坐。村里人见他们终日守着这片树林,明里暗里都在嘲笑,4人团队中开始有人动摇,唯独姚其学和李福泉在咬着牙坚持。
3年挂果,5年丰产。不过,在迎来丰产的1992年,销路又是另一个问题。
姚其学等4人想出了一个“笨”办法。他们装了满满4篓梨子,一人背上一个,向马场坪走去。10公里路程,徒步一个多小时终于能坐上去往都匀的班车,再摇晃一个半小时,才停在都匀开发市场门口。下了车,姚其学等人背着沉重的背篓一头钻进热闹的市场中去。
4位风尘仆仆的农民给市场里的每个水果摊摊主免费送两个梨,邀请品尝。在市场的尽头,一位年迈的老太太坐在路边,摊位前摆放着一些水果,沉默不语。姚其学照例掏出两个梨子,恭谨地递到对方手中,老太太并没有接,不屑地说道:“我从民国活到现在,什么没有吃过?你这梨子太硬了,咬不动!”
姚其学不急不恼,找来水果刀削下一块递给对方:“您就尝一小口。”老太太勉为其难咬了一口,顿时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来,浑浊的眼神也明亮了几分,道:“你这味道我从民国到现在都还没吃过哟。你还剩多少?我全要了!”
姚其学摆摆手,笑着说:“你要是喜欢,这里也没剩多少,我都送你了,以后再来卖!”
这趟都匀之行虽然一分钱没挣,但在不久之后,便有人从都匀专程赶来,以每公斤2元的价格进行收购。那时,猪肉也才卖4元钱一公斤。
果林场终于走上正轨,村里冷嘲热讽的声音不知何时已全然消失,但这片果林也越来越不清净。姚其学和在这里务工的农民们抓了好几回偷梨子的人,其中一个让他尤为震惊,一晚上竟坚持不懈摘了70多公斤的梨。愤怒之余,姚其学也感到无奈,“日子太困难了,村民们吃不饱饭,当然会眼红。”他知道问题的根源,而作为当时生产队的队长,他自然也有责任和义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995年,果林场的梨子供不应求。姚其学开始不计回报地动员村民们种植这种被命名为“金谷富梨”的品种。双谷的梨树林漫山遍野铺开,果林场里的“盗梨贼”也从此不见踪影。
转眼到了2004年,双谷乡变成了双谷村,在福泉市的重视下,大小项目陆续向双谷倾斜,梨树林扩张到了数千亩。在乡镇领导的提议和福泉市旅游部门的支持下,2005年,双谷的白色花海迎来了不少游客,福泉首届金谷春雪梨花节成了这里旅游发展的起点。在30年中不断更新迭代、持续优化的“金谷富梨”,也于2018年以“福泉梨”的名字被农业农村部正式批准进行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姚其学退休后,李福泉挑起了村支书的担子。2018年,李福泉专程去了一趟修文县,在这个猕猴桃种植大县学习技术,引进了猕猴桃的种植。水晶葡萄、巨峰葡萄、杨梅、猕猴桃……各类水果陆续在双谷生长起来,游客对采摘乐此不疲,而回到双谷村经营农家乐、种植果树的村民也越来越多。
姚其学乐于看到双谷村热闹的情景。“梨子好了,外出打工的人就少了,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也少了,人均年收入有1.3万元!你晓不晓得,我们双谷现在是全国农业旅游示范村、国家3A级风景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梨花节都办了14届了!”他脸上溢满喜悦。
“是头牛你就来种果树,要是狐狸那就算了。”30多年前,果林场一分场场长李声益说的这句话,李福泉一直记到现在。50多岁的他,笑起来依然带有一丝腼腆,他自认自己就是那头牛,埋头耕耘,最期待的就是见到来年满山梨花再开放。
一审:罗忠显
二审:付芳婧
三审:罗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