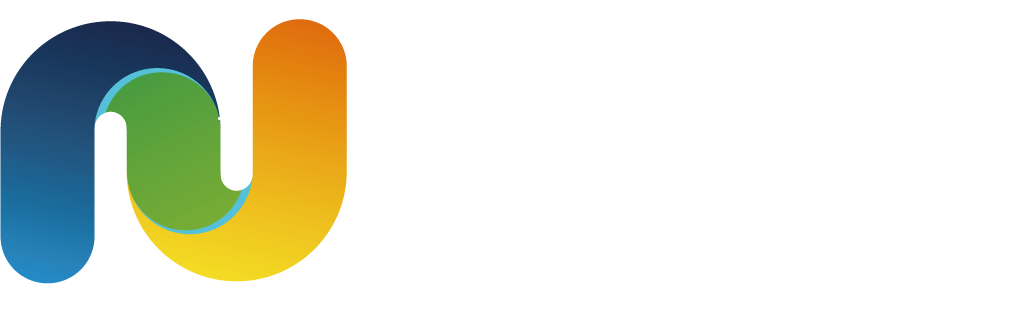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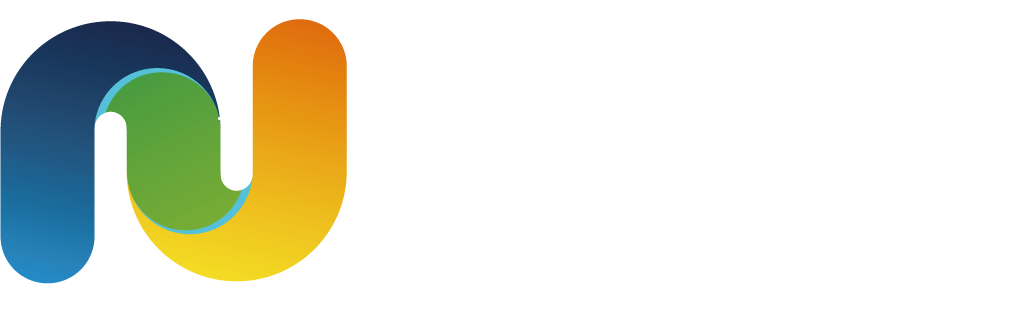
贵州是多民族省份,17个世居少数民族分布于此,全省少数民族人口总量在全国排第四位。或许正是因为这特别的“因缘”,读者常常能在《新黔中行》里读到一些专属于贵州少数民族村寨的新趣瞬间。
“蜡染服装走上国际T台”“苗寨掀起时尚风潮”“布依意蕴的小众民宿”……这些有故事、有新意的少数民族村寨在创新型转变中,打破了人们对乡村局限性的传统认知,并不断在建设美好乡村的路上求取“更优解”。一边保留乡村的独特性,一边开拓乡村的现代性,在提升“颜值”中提高“价值”,绘制出乡村振兴路上的多彩画卷。
因地制宜开发布依文化、融合创新发展乡村旅游是贞丰县纳孔村的发展基调。旅游激活了当地的生态、文化和闲置资源,乡村空间变得更加开放,吸引了外流人口的回归。在《贞丰县纳孔村:专注旅游的村寨》一文中,村支书岑立江就是抓住时机最早返乡的那一批人,旅游的“引流功能”为当地人带来了红利,也让这个布依村落一改旧貌,变成了热闹的“人气村”。
有“庖汤第一村”美誉的乌当区王岗村也是一个布依族村寨,与纳孔村不一样的是,布依美食是这里的“主角”,成为发展经济的特别资源和个性IP。在《乌当区王岗村:好香的村庄》一文里,韦登亮和花葵敢于第一个吃螃蟹,他们利用“庖汤”这种自带“氛围感”的少数民族传统美食开办农家乐,为王岗村打造出一张响亮的美食招牌。
兴仁市鲤鱼村是一个苗族与布依族混居的村寨,发展滞后曾困住了许多人的脚步,无法“跳跃”。作者在《兴仁市鲤鱼村:带着乡民“跃龙门”》一文中这样写道:“鲤鱼村虽然人口多、面积大,村集体经济却一直萎靡不振。”为了解决问题,村委会主任田锦华将目光放在产业发展上,带领村民种桑养蚕,调整了乡村的功能定位,释放出土地的多元价值。
从“藏在深闺人不识”到“多向开放换新颜”,少数民族传统村寨的转型升级体现了我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广度和深度,呈现了乡村建设的多样化与个性化,也提振了人们共同富裕的信心。这份信心与底气坚定了岑立江、韦登亮、田锦华等乡村建设者们走脚下的路,激励人们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踏上时代新征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路上不掉队、不缺席,创造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
—— 向秋樾
美丽乡村的旅游发展之路
贞丰县纳孔村:专注旅游的村寨
顺着蜿蜒的三岔河沿岸行驶,窗外的风景大致勾勒出者相镇纳孔村的模样。
统一风格的布依族民居结合现代审美,既有实用性也不落俗套。常见的波斯菊有1米多高,游人一头扎进花丛中,像潜入一片五彩斑斓的海洋一般。工作日的露营基地游客稀少,帐篷随意散落在视野开阔的草坪上,仿佛还能感受到天亮前的狂欢氛围。
显然,这已不是一个普通的村庄。无论是地里种的、村里建的,还是河里游的,所有的东西都在明确地为一件事情服务,那就是旅游。一切以发展旅游业为基本原则,让贵州西南地区的这个布依族村寨懂得如何自我经营,就连路边经营小店的村民,也因常年与游客打交道,早已习惯了天南地北的口音,和谁都能聊上两句。
见到村支书岑立江后,他果然三句话离不开“旅游”二字。
“村里有好几个公司,县里的旅游平台公司最早入驻,对纳孔村的旅游进行开发和管理;浙江商会的公司主要经营客栈、酒店。有一个水上娱乐公司,开发水上项目。还有个公司专门开发‘夜经济’。我们村级合作社在2015年就成立了,打造了花海,也参与一些项目开发……”岑立江滔滔不绝,将参与纳孔村旅游开发的机构如竹筒倒豆子般细细数来。
据岑立江所说,纳孔村的旅游发展意识早在2004年就已觉醒,“可以说,在整个者相镇,我们纳孔村的发展一直都是走在前面的。我认为这多少和村民们见多识广有关系。”
过去,纳孔村老屋场组是者相镇的集市所在地,赶“老屋场”早已成了者相镇人们的共同记忆。南来北往的人们汇聚于此开展交易,在讨价还价中不断打磨,纳孔村的人所掌握的生意之道多少比其他人更多一些。“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们村的人就懂得用反季节水果来提高收入了。”岑立江毫不掩饰对这套“生意经”的赞赏。
那时,不少地方兴起一阵种植椪柑的风潮。每年十一二月,椪柑大量上市,但很快就因为产能过剩导致跌价。聪明的纳孔村人并没有被市场左右,他们通过地窖等将椪柑进行储藏保鲜,直到春节时才推到集市上进行销售。如此一来,过去每公斤只售2元钱的椪柑,在春节能售出每公斤6元钱的高价,巧妙的时间差,让纳孔村人挣得盆满钵满。
这种举一反三的能力,在岑立江看来已经刻入了纳孔人的骨血里,包括他自己也十分善用这种思维。
1997年,岑立江便外出务工。在城镇化建设刚刚兴起时,他选择了一门新兴的产业——制造罗马柱。这种充满异国风情的建材在当时并不多见,岑立江自然能占领不小的市场。10年后,他回乡建起了村里第二栋具有现代风格的砖瓦房,之后,便被推选为村委会主任。
此时的纳孔村,在整个贞丰县已小有名气。这个布依族村寨临近绵延10余公里的三岔河,民族风情浓郁,加上2004年“贞丰布依族风情节”的助推,更是让人们对纳孔村十分向往。过去,唯一阻拦此地旅游发展的只有交通问题,泥泞的小路让不少人望而却步,直到2008年并村之后,贞丰县提出将三岔河打造成景区,纳孔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也陆续开始启动。
回乡当上村干部的岑立江,亲眼见证了村里的变化。短短几年,县里的统一打造让纳孔村彻底换了一副面貌,一些嫁到村外多年的妇女,回乡探亲时甚至找不到娘家的老屋了。
随着贵州省浙江商会被引进到村里进行投资,客栈、民宿、农家乐在当地兴起,到2015年,村里的农家乐多达二三十家。有丰富生意经验的岑立江,眼看着村里的游客越来越多,便和妻子决定赶一趟“时髦”,定制了一辆餐车在景区里售卖炸洋芋、凉粉等小吃,仅一年的时间,他们竟挣了10多万元!
当然,这一年里,村里也没有歇着。由于景区内项目单一,不利于长远发展,村里便筹资成立了村级合作社,流转100多亩土地,开发花海项目。在流转土地这个问题上,岑立江等村干部可以说是胜券在握。仅需简单开会动员,村民们便积极响应,原因非常简单,人们很早就意识到,种植粮食只能填饱肚子,还不如把土地进行整合,还能增值。
花海成功打造,村里的基础设施同步得到进一步提升,就在此时,岑立江见到了一位老朋友。
这位老朋友是隔壁猫坡村的村民黄汉权。他在部队当了8年兵,2011年退役回乡后,与父亲在纳孔村经营一家民办学校。2016年,民办学校由于种种原因停办,黄汉权便在纳孔村租来一片土地开办起了农家乐。到了2017年,他再度找到岑立江等村干部商量,提出希望再将民办学校的那块土地租过来,开办新的农家乐。
双方一拍即合,曾经的校舍被改造为16间包房和8间民宿,操场也被一分为二,一边用来停车,一边摆了15张桌子,农家乐的名字则定为“珉权山庄”。贞丰县和者相镇对纳孔村不遗余力地宣传,间接帮助黄汉权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很快,他的山庄为10余位村民提供了岗位,每人每月能挣到2600元到3000元不等的工资。黄汉权早在退役时就对乡村生活心生向往,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短短几年,就能在老家用这种方式回归田园。
离开珉权山庄,岑立江带着我登上横跨三岔河的那座大桥,桥头精心设计了停车的区域,桥上也标示了最佳拍照视角的位置。三岔河的河水在我们脚下向东缓缓流去,推出层层叠叠的波纹。桥下,有人静静坐在岸边垂钓;桥上,游客举着手机拍下美景。岑立江又说起了旅游的事:“你知道的吧?2015年的时候,纳孔村就获批为贵州省首个民族文化旅游扶贫试验区,2020年又入选世界旅游联盟减贫案例。我们不打算把心思花在其他种植养殖产业上,就算要种点什么,那也是要为旅游服务的。”他说这话时,看起来无比坚定,显然心里已然有了一个计划。
兴仁市鲤鱼村:带着乡民“跃龙门”
去鲤鱼村那天恰好是当地苗族的传统节日“八月八”。可惜,待我下午抵达鲤鱼村时,欢庆节日的人群早已散去。在下沉式广场中,有人在烤酒。一支细细的竹筒从蒸笼边伸出,剔透的液体缓缓流淌,热气裹着甜蜜的酒香钻进人们的鼻孔,几个男人聚在离锅不远的地方席地而坐,静静等待。
闲逛一圈,回到村委会办公室。约莫20多分钟之后,一个黑色的身影像风一样“刮”进办公室,径直向我走来。他气喘吁吁地伸出右手,抱歉地说:“你好,久等了,活动刚刚弄完,我们去楼上聊吧。”说罢,便顺手拿上两瓶水,直冲二楼会议室。
黑皮肤、圆脸,不笑的时候看起来十分严肃,直到在二楼会议室坐下,我才有时间看清他的长相。他是田锦华,鲤鱼村的村委会主任。之所以如此紧迫,是因为他留给我的时间只有不到1个小时,结束与我的交流之后,另一拨媒体即将到达,他必须在场。
“实在不好意思,事情太多太杂,现在头都是晕的。”田锦华有些无可奈何,他恨不得把一分钟分成两分钟来用。看着这位年龄不到40岁,却一脸疲态的村委会主任,我不忍心再对他的身世和经历刨根问底。可哪怕是最熟悉的村里的工作时,他也会突然迷茫起来:“故事实在太多,一时间不知该讲哪个好。”
如果见过10年前的鲤鱼村,或许就能明白,为什么这里现在会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鲤鱼村是一个典型的苗族与布依族混居的村寨,有1000多户、近5000人,正是因为人口多、产业少等问题,在管理上并不轻松。2011年5月,国家领导人来到这里考察,鼓励鲤鱼村的村民们“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努力用自己的双手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好的新生活”。这次考察,无疑为鲤鱼村注入了新活力,不过,变化并没有那么快发生。
田锦华生于鲤鱼村的苗族寨子,20多岁时就被推选为村委会主任。那是2013年,鲤鱼村正酝酿着变革,希望向旅游景区的方向发展。变革必然会带来矛盾,这矛盾的源头又大多与土地有关。无论是修路、改造房屋,还是兴办产业,每次村里即将迎来新的改变时,田锦华总会因为与村民们协商土地的问题而苦恼。
村委会主任这份责任像一只大手,推着他只能继续往前。修路时,他挨家挨户动员做工作,从村里老人的口中,了解到人们为什么如此珍视土地的原因。“以前饿怕了,有土地就能种粮食,就不会挨饿。”理由越朴素反倒越令人心酸,年轻的田锦华尽可能与老人们感同身受,也耐心向他们解释通组路、窜户路的概念,慢慢做通了村民的工作。
修路这道“坎”他终于迈过了,但另一道“坎”就像一座大山,有些难以逾越。
鲤鱼村村集体经济一直萎靡不振。田锦华在外经营着自己的生意,自然明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如果村里能有一项代表性的产业带着村民们一起挣钱,不仅能填满大家的荷包,忙碌起来的人们或许也没时间去喝酒、闲逛,无所事事了。
2017年,田锦华去兴仁市参加一个脱贫攻坚的相关会议。会上,市里的领导提起“东西部扶贫协作有500万元资金,可用于产业发展”。500万元,这个数字让田锦华瞬间来了精神。回到村里后,他与驻村第一书记商量:“我觉得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政策,弄点资金过来把我们村的产业搞起来。具体搞什么,还得先去考察一下。”
田锦华带着村干部和群众代表,前往广西平果、隆林以及凯里、西江、兴义等地进行考察。每次回来之后,又开群众会动员大家出谋划策,对项目进行缜密地分析和研究。最终,田锦华确定带动村民们发展种桑养蚕的事业。
这对鲤鱼村的人来说不是难事。尤其是苗族村民,他们身上穿的衣服大多都是从育蚕缫丝开始一步步制成的。不过,产业启动之后,传统养殖与现代技术的矛盾很快便凸显出来。“我们世世代代都是这样放在簸箕里养,会有什么问题呢?”自诩经验丰富的村民,完全无法理解为了养蚕不仅要建个厂房,还要换一种养法。田锦华只能四处求教技术专家,一遍遍为村民们培训,同时也一如既往地耐心解释何为“产业化”。
时光匆匆流走,鲤鱼村的种桑养蚕渐成规模,旅游业也日渐兴旺。村里,农家乐、民宿客栈接二连三开门营业,做刺绣、蜡染的妇女们也将手艺带到了景区中。那户曾经接受领导考察的农家,早已将房屋改建成农家乐,取名为“和谐人家”,成了游客常去的“打卡地”。
而田锦华仍未来得及休息一下。他获得了一次前往上海考察的机会,在那个充满时尚气息的国际都市中,当地蚕丝被的标价让他惊掉了下巴。“2万多!”他反复端详着这床被子,心想:“这和我们村出的蚕丝被完全没有区别啊!”可鲤鱼村的蚕丝被统一定价都在380元至450元之间。还是品牌和包装的问题,田锦华明白个中道理,做响品牌的想法在他脑海中滋生。
很快,“和谐人家”被定位为当地的公共品牌,无论是苗绣、银饰还是农特产品,皆可运用这一品牌进行包装。而对于心心念念的蚕丝被品牌,田锦华也在做着尝试,计划申请新建工厂,进一步完善当地蚕丝被的制造和包装。
风风火火往前冲的田锦华,在出任村委会主任七八年后,陆续收获了不少表彰。2021年年初,他登上去往北京的飞机,来到人民大会堂,接过了“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的称号。不过,对于这些表彰,他自己倒鲜少提及,“这几年做下来,零零碎碎太多事情,你让我说哪一件,我一时也想不起来。不过,既然挑起了这个担子,就要好好地做下去,这么多双眼睛看着你,要给大家一个交代。”
匆匆结束了聊天,田锦华又像一阵黑色的旋风般,“刮”出了办公室。夕阳西斜,我再来到鲤鱼民族广场上,那口烤酒的大蒸锅还在冒着热气,忙碌的农妇正舀起一勺酒递到游客嘴边。不远处的草地上,几位微醺的苗家汉子聊着天,笑声传得很远。
乌当区王岗村:好香的村庄
虽然,新堡布依族乡的7个村寨各有各的风光,但我此行的目的地却并非为了赏景,而是为了一口美食。非常不巧的是,我到来的这天,被誉为“庖汤第一村”的王岗村里正在为一位已逝的长者筹办白事,几乎全村的农家乐都关门歇业。
尽管如此,我依旧见到了那位当年第一批在王岗村以做“庖汤”为业的人。
在村委会,一位瘦高的男人招呼我们坐下,又转身出门招呼来客。带我来王岗村的乡里面负责外宣工作的韦登亮说起了新堡布依族乡的故事。
新堡布依族乡大概是贵阳、乃至整个贵州最早开始推行全域旅游概念的地方,从2007年起,整乡7个村庄就已陆续吃上旅游这碗“饭”。7个村庄各有所长,拥有香纸沟景区资源的陇脚村,最早端起了旅游的“饭碗”;被誉为“高原画乡”的陇上村,凭借当地的农民画特色打响了招牌;据说当地布依族历史能追溯到殷商时期的大寨村,则将古老文化作为自己的标志……此外,还有新堡村、马头村、长坡村等也都有自己的风格。而被誉为“庖汤第一村”的王岗村,其金字招牌就是布依族美食。
正聊到兴起,那位和我们匆匆打过招呼的男人再次走进屋里,郑重其事地伸出右手。韦登亮介绍:“这是刚换届新当选的村支书花葵,也是村里最早做农家乐的人之一。”
花葵早在1998年就进入村委会工作了。2007年换届后,他在乡党委政府的安排下,来到离王岗村不远的香纸沟景区工作。
20世纪90年代初期,陇脚村的村民们已经靠香纸沟景区开发,做起了小生意,开起了农家乐,这让其他除了黄土就是大山的村庄只有羡慕的份儿。在景区服务中心工作的花葵,更是每天都在变着花样地“受刺激”。
花葵的羡慕并未持续多久,工作几个月后,他就听到消息,乡党委政府计划推动王岗村发展旅游,准备先带动几户村民开办农家乐作为示范,主要经营“庖汤”生意。乡党委政府向花葵抛来邀请,这正好完美契合了花葵的期待。
“庖汤”是布依族人宰杀年猪时吃的第一顿火锅。通常,布依族农家宰杀年猪时会有诸多亲朋好友前来帮忙,辛苦一天后,主人家便会取大块肥瘦相间的好肉,加上肠子等杂碎,以及凝固的猪血,烹制成一锅美味鲜香的火锅,用来招待客人。好客的布依族人,在端菜上桌时通常会客套一番,说:“大家辛苦一天,也没有什么吃的,只好请大家吃点庖汤剩水,不要客气!”人们则围着这一大锅新鲜的美味赞美道:“你这‘三盘四碟八大碗’的,哪里是什么庖汤剩水?”说罢,便大快朵颐起来,杀年猪的热闹气氛也在鞭炮声中被烘托得更让人心潮澎湃。
让村民开办农家乐专做“庖汤”的主意,让王岗人感到不可思议。乡党委政府和王岗村的村干部们,对5户村民展开苦口婆心的动员攻势,除了花葵跃跃欲试之外,只有花兵和罗应顺两位相对年轻的村民同意尝试。锅碗瓢盆、桌椅板凳,开办农家乐所需要的器具,都由乡里和村里统一提供支持。除此之外,又请来相关专家提供建议,将布依美食的“三盘四碟八大碗”作为庖汤宴的主要内容。王岗村的庖汤盛宴就这样缓缓拉开帷幕。
在“去香纸沟游玩,来王岗吃庖汤”的宣传攻势下,农家乐很快开始盈利。眼见3位率先尝试做生意的村民有了收获,其他人也开始蠢蠢欲动。
谁知,好景不长。2008年,贵州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凝冻灾害,王岗村门可罗雀。苦守了近一个月,陆续有跟风开店的村民忍受不住,索性关张。可花葵和另两位最先开店的村民都不甘心,加上村干部们每天提心吊胆地前来打探,旁敲侧击地劝他们:“坚持,再坚持!”好歹算是保住了这几家坚守阵地的农家乐。
灾害过后,旅游行业开始回温。2009年,生活得到极大改变的花葵,给自己正在贵阳某家电销售公司工作的弟弟花兴江打去电话。
“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600多吧。”
“不要干了,回来搞农家乐。”
花兴江知道农家乐的回报有多丰厚。他和妻子果断收拾好家当,头也不回地辞职回到家乡。两兄弟的生意扩大了规模,做得风生水起,而新堡布依族乡又有了新动作。
王岗村的变化越发剧烈,房屋变得更漂亮,路也越来越宽,看起来更像一个适合休闲旅游的美丽小村庄了。2010年,贵阳市旅发大会在乌当区召开,乌当区也借势推出了“泉城五韵”乡村旅游度假区项目,将偏坡、陇脚、渡寨、王岗、阿栗等村镇进行连片打造,每个村镇都有不同的定位,而以“能吃肉是福”为特色的王岗,则被定位成“福韵·王岗”。一时间,村里的农家乐扩充到几十家,而没有条件开办农家乐的村民,也靠种植蔬菜、养殖生猪,为村里的农家乐提供货源,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2014年,当地引进了旅游企业,依托温泉优势在王岗村打造出枫叶谷景区,主打水上娱乐。2016年正式开业后,生意持续火爆,村里与景区展开紧密合作,王岗村的村集体收入也有了着落。
讲起王岗村化身“庖汤第一村”的这10多年,花葵在喜悦中又生出感叹:“如果没有当初乡里的整体打造,也不会有今天的王岗村。如果没有过去这几届村支两委的坚持,许多人可能都挺不过2008年的那个冬天……”眼下的王岗村,早已围绕“庖汤”形成一条产业链,人均收入从过去的2000多元上涨到29000多元。王岗村的名声也早已传到省外,而花葵如今也被推选为新一任的村支书,他清晰地感受到压力在肩,但也信心十足。
不知不觉已到中午,理应是王岗村最热闹的时候。不过,今天的王岗村有些特别,因为德高望重的老人过世,几乎所有农家乐都关门谢客。韦登亮说,这是王岗村人淳朴的习俗,谁家有大事,人们宁愿不做这一天的生意,也要为同村人出一分力。村里安安静静的,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气味,虽然不知是不是庖汤的味道,总之依旧很香。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彭芳蓉)
一审:罗忠显
二审:付芳婧
三审:罗曦
